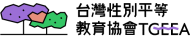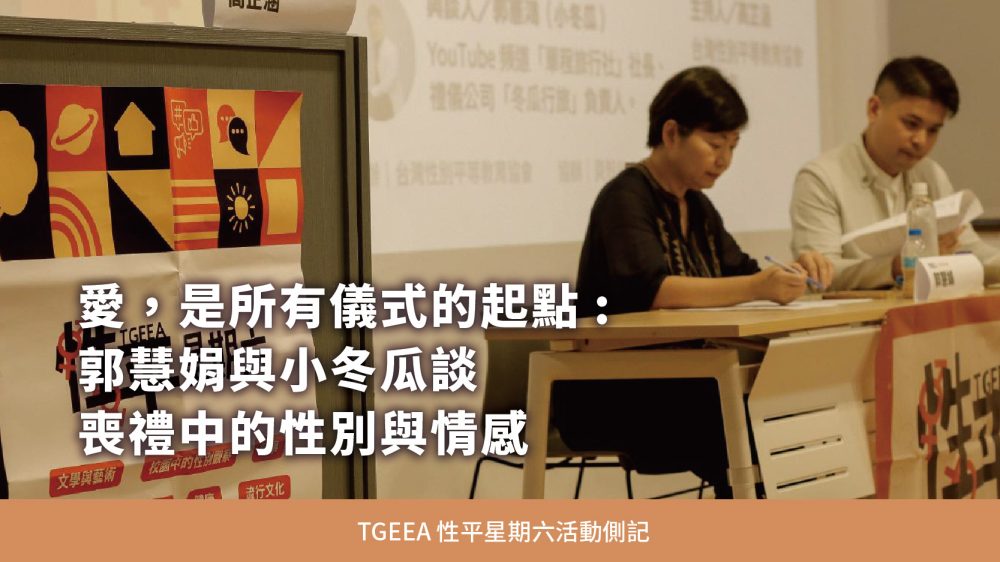- 時間:2025 年 7 月 5 日 14:00-16:00
- 地點:貝殼放大糖廍 C 倉多功能交誼廳 (台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132-7 號)
- 講師:郭慧娟(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理事長)、小冬瓜(YouTube 頻道「單程旅行社」社長)
王柏文(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實習生) / 整理撰寫
在七月份的「性平星期六」系列講座中,我們邀請到郭慧娟老師及郭憲鴻(小冬瓜),分享他們在生死教育及殯葬推廣工作中的實務經驗,並從這些經驗出發,帶領我們探討殯葬習俗中暗藏的性別不平等,以及該如何以嶄新的實踐方式達到尊重傳統與接納多元之間的平衡。

死亡面前人人平等?靈堂裡的隱形規則
講座開場,郭慧娟老師便拋出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:「死亡真的是平等的嗎?死亡的儀式安排裡,是否有長久存在的不平等議題,是我們沒有注意到的?」
他指出,自己在提供殯葬規劃建議與參與評鑒的工作中,時常注意到女性在儀式當中的缺席。即使逝者生前與女性親屬關係密切、由女兒長期照顧,喪禮上負責各個儀式環節的人,卻往往還是男性。女性不僅經常被排除在參與者之外,就連在訃聞中的稱謂,也經常被省略。
他進一步質疑:「為什麼儀式中一定要有一個性別僵化的框架?」他強調,既然家庭面貌多元,喪禮儀式也應該根據實際家庭情況進行調整,而非一味遵循傳統的制式規則。

當照顧者無法回家:女兒的矛盾與壓力
在傳統文化裡,父母過世的照顧責任時常落到女兒身上。尤其是在少子化與單親家庭日增的今天,許多家庭「只剩一個女兒」,而他便成為理所當然的承擔者。但郭慧娟老師指出,即使女兒在照顧上付出最多,卻仍可能因未婚、非直系繼承等理由,被排除於祖先牌位之外。
他直言,這些女性常常被推著要「平等」,但社會卻沒給他們一個真正屬於「家庭一份子」的位置。「生前照顧,死後分不到財產,連回家的資格都沒有」,他感慨地說,這種「死後不能回家」的觀念根源於過去婚姻是女性唯一出路的時代,而現在的社會早已不同,卻仍未能修補制度空隙。
傳統的依據,僅僅只是一句「阿災」?
針對女性與多元性別者是否能參與儀式、使用恰當稱謂,郭慧娟老師曾多次向從業人員提出問題:阿姨或姑姑能否封釘?女兒是否能念哀悼詞?多元性別的子女又該如何出現在訃聞中?但他坦言,這些提問不但會遭到從業人員的否定,甚至被罵說「亂七八糟」。
更令人感慨的是,即使是堅守傳統的長輩,在被追問「為什麼」時,答案往往只有一句「阿災」,又或者是「大家都這樣做」。他舉例,許多長輩相信「夫妻不能相送,因為送完會被帶走」、「送完就要再嫁」──這些說法與現實脫節,卻仍深植於人們對死亡儀式的理解中。
他質疑「明知道照做會造成悲傷與遺憾,為甚麼我們一定要照做?」當奠基於過去社會所建構的傳統習俗,已經無法完全適應當代情感與家庭結構的時候,照樣做真的有其必要嗎?

誰能站在儀式中心?不是性別,而是關係
郭慧娟老師主張,殯葬儀式中每一個環節都應該交由「最適合的人」負責,而不是依照性別分配工作。在生死教育工作者與性平倡議者的努力下,過往由男性主導的環節──如執杖、捧斗、持招魂幡等──如今逐漸也能交由女性擔任,訃聞用詞也開始出現「孝女」、「孝子女」的選項,不再只寫「孝男」。
但他強調,這些轉變並非自動發生,而是來自業者與家屬之間大量的對話與磨合。在持續的溝通中,人們得以重新理解儀式的意義,從而願意鬆動固有的性別分工,逐步向真正的平等靠近。
在推動改革的同時,郭慧娟老師也提醒,檢視與調整傳統習俗不該只是「為改而改」,而是應建立在有依據的基礎之上。他指出,目前內政部已推出殯葬禮儀相關指引,可提供殯葬從業人員與家屬參考,使改變有章可循、減少家屬的不安。
不強推理念,而是提供選擇的可能性
作為殯葬第一線的從業人員,小冬瓜從實務出發,提出了另一個角度的思考。
「喪禮的安排,其實藏著很多性別分工。」小冬瓜指出,從祭拜順序、誰能參加、穿什麼顏色的衣服,到誰被視為「自己人」,傳統殯葬制度裡性別角色深植其中。他表示,台灣雖然在性別平等指標上名列亞洲前茅,但在實際儀式安排上,許多性別區隔仍根深蒂固。不過,他也觀察到,傳統正一點一滴被鬆動,尤其是在北部的都會區。而這個過程,最關鍵的不是推翻舊有制度,而是「尊重」。
他分享,早期獲取資訊的管道較為單一,社會大眾的價值觀較為一致。但如今媒介分眾、立場分化,價值觀的落差日益明顯。這種分歧不僅體現在音樂、政治,也反映在對死亡、儀式與性別角色的理解上。因此,他強調:「無論理念多前衛,也要學會尊重。提供選擇比要求接受更重要。」

資訊分眾化的社會,價值觀落差愈來愈大
在談到改變的難度時,小冬瓜指出,台灣社會的資訊獲取已高度分眾。以流行文化為例,他提到:「以前大家都聽電台,蔡依林出新歌大家都知道。現在資訊來源分得這麼細,很多事情可能你知道,但對方完全沒聽過。」這樣的分眾現象也延伸到性別議題,甚至政治立場。
他感慨,在這樣的社會中,即使表面上「女性可以當總統」已成常態,但很多人仍會在性別議題上反對「性平」的實質改革。即使不是出於性別歧視,也會說「男女有別」、「這不是尊卑的問題」。他表示:「傳統家庭就是靠這種觀念維繫,一旦談多元性別,只會讓人更混亂。」
對此,小冬瓜的原則是:「如果多元性別認同能讓家屬更得到安慰,那我們就會做。」他指出,家屬在面對死亡時,已經需要處理大量事務與情緒,如果這時又強硬推廣觀念,只會增加對立。「所以我們會觀察,有需要時才提供這樣的服務。」
從儀式引導到理解情感:指引與教育的力量
小冬瓜亦以「封釘」的儀式為例,傳統封釘皆由男性負責執行,但現在從業人員會透過提問,引導家屬說出內心的想法。這不只是讓儀式更貼近個人需要,也是協助家屬重新參與其中。
他表示,現今社會逐步邁向多元,但許多殯葬制度仍以異性戀家庭為預設框架。這也讓從業人員處於「被動應對」的局面。不過,有了明確的操作指引後,服務人員便能從被動轉為主動,在儀式設計初期就向家屬介紹多元選項,打開理解與選擇的空間。
「這是一條很辛苦的路,但我們在努力。」他強調,這樣的轉變需要長時間的熏陶與教育,不是一次性的說服,而是日積月累的社會對話。

面對多元家庭與未來世代:喪禮也該與時俱進
小冬瓜指出,許多傳統喪禮環節,例如壽衣款式,至今仍未真正「進步」過。當家屬猶豫「要穿西裝還是穿裙子」時,便已可以從中看到,真正的問題其實是:我們是否理解逝者的性別身份與自我認同?他曾遇過家屬討論「如果這位生理男其實更想穿裙子呢?」這類問題,正顯示出儀式與性別已不再是二分法能解釋的。
「有些人不想被定義,他們說就叫我『摯愛』就好。」他分享,這樣的稱謂反而更貼近逝者與家屬之間真實的情感。
他也觀察,許多傳統訃聞內容已經不符當代生活。從過去「族繁不及備載」,到如今很多人沒有子嗣,剩下的篇幅不妨用來放文章、照片或逝者喜愛的事物,甚至曾有企業家以家庭樹的形式撰寫生平,不分男女,平實地介紹每位親屬,也是一種新的書寫方式。
喪禮的核心,是讓人感受到情感的照顧
「儀式是要服務人,不是人去服務儀式。」
小冬瓜指出,從事殯葬工作多年,他深知每場儀式背後真正重要的不是形式本身,而是人們是否能在其中獲得慰藉。
他分享,有人選擇安樂死,在死亡前一個個向親友道別;也有人在靈堂請來猛男發雞排,留下充滿笑聲的離別儀式。這些看似不合傳統的作法,正反映了當代社會的價值轉變。雖然這樣的安排可能引來批評,但那份情感是否真實、是否符合逝者與家屬的想望,才是最值得思考的核心。

愛,是所有儀式的起點
「今天我們談的,不是為了性平而性平,也不是為了打破傳統而戰,而是為了延續愛。」郭慧娟老師強調。他認為,儀式的本質應該是傳遞與表達愛,而非僵化地重複無意義的形式。
他指出,許多傳統儀式的安排,常常讓人陷入「要不要照做」的掙扎,但若能以「如何讓愛被看見」為出發點,形式的爭議就不再是焦點。他強調,儀式的每個環節,不只是為了完成某種「規矩」,而是能否真正安撫生者的情感、理解逝者的心願。
「破地獄,不只是讓亡者脫困,也是讓生者放下遺憾。」郭慧娟老師認為,好的儀式應能撫慰傷痛、分享悲傷,也教會人們如何道謝、道歉與道別。無論形式如何改變,「如果能因此讓人被看見與被愛,那這就是一場成功的喪禮。」

當死亡不再是禁忌:從預囑到天堂旅行箱
在談論制度與文化的革新之餘,郭慧娟老師也分享了自身的實踐經驗,示範了如何將「死亡自主權」落實於日常。他指出,台灣在醫療制度上已逐步推行「病人自主權利法」,而《殯葬管理條例》第65條亦明訂,若逝者生前已對其喪葬方式有明確交代,家屬與從業人員便應予以尊重。他強調,隨著高齡與獨居人口增加,越來越多人需要面對「沒人替我決定」的處境,因此自主規劃成為不可忽視的議題。
他以自己為例,為了減少遺憾與衝突,特別設計了「五種臨床情境」下的醫療應對計畫,包括:失智、自然衰老、急重症限時救治等情況是否插管、是否使用葉克膜等設備。他也明言,身後不希望有傳統焚香紙錢、拜飯的儀式,改以鮮花代表心意,同時也考量環保永續。
為了讓家人能夠清楚掌握相關資訊,他準備了一只「天堂旅行箱」,內含重要文件(如保單、身分證明、自書遺囑、意定監護契約)、財務紀錄與數位遺產的帳密清單,甚至包括他的美照與葬禮音樂。他笑說:「鞋子不能放高跟鞋,不然頭七走回來時會喀喀喀的響。」這份旅行箱除了實務功能,也包含五張信卡,道愛、道謝、道歉、道別,以及一張象徵「新生」的生日卡,象徵生命的溫柔告別。
而同場講者小冬瓜也提到,自己身為從業人員,也早已開始準備屬於自己的天堂旅行箱。
「談死,並不代表放棄,而是讓愛與安排可以被延續。」